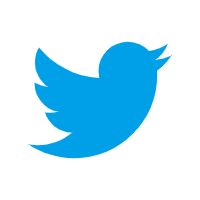主角出场
按常理,撒谎是为了欺骗某人,从而得到某种好处。但是他编造一场癌症又有什么可赢的呢?奇怪的是,他想到自己没什么道理撒谎禁不住笑了。这笑,也同样令人大惑不解。他为什么笑?他觉得自己行为有趣吗?不,理解有趣本来也不是他的强项。就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象中的癌症教他高兴。他继续走自己的路,继续笑。他笑,为自己的好心情感到高兴。
别笑。说话而又不引人注目,不容易!一直在人前讲话,而又不被人听在耳朵里,这需要精湛的技艺!
木偶剧
时间过得飞快。幸亏有了时间,我们首先是活着,也就是说:被人控诉、被人审判。然后我们走向死亡,我们跟那些认识我们的人还可以待上几年,但是很快产生另一个变化:死的人变成死了很久的死人,没有人再记得他们,他们消失在虚无中;只有几个人,极少数极少数几个人,还让他们的名字留在记忆中,但是由于失去了真正的见证人、真实的回忆,他们也变成了木偶……
假使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这个故事由真人演,那是在蒙人了。没有人有权利去装模作样重现一个已不在世的人的生平。没有人有权利凭一个木偶去创作一个人。
我才瞧不起我们那些名字给马路冠名的大人物。他们出名是来自他们的野心、他们的虚荣、他们的谎言、他们的残酷。唯有加里宁其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是纪念每个人都有过的一种痛,是纪念一场绝望的斗争,这场斗争除了对自己从未对他人造成过痛苦。
一阵沉默后,拉蒙说:“阿兰,你说得合情合理。我死后,要每十年醒来一次,来证实加里宁格勒是否还是加里宁格勒。如果依然不变,我跟人类还是意气相投的,跟其重归于好后再回到我的坟墓里去。”
一根小羽 在天花板下飘
黑格尔在他对喜剧的反思中,说真正的幽默没有无穷的好心情是不可想象的,请听好,这是他说的原话:‘无穷的好心情’,‘unendliche Wohlgemutheit’。不是取笑,不是嘲讽,不是讥诮。只是从无穷的好心情的高度你才能观察到你脚下人类的永久的愚蠢,从而发笑。
请好好理解我,我梦见的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不是未来的一笔勾销,不,不,我期盼的是人的完全消失,带着他们的未来与过去,带着他们的起始与结束,带着他们存在的全过程,带着他们所有的记忆,带着尼禄和拿破仑,带着佛祖和耶稣,我期盼的是根植于第一个蠢女人的无肚脐小腹内的那棵树彻底毁灭——那个女人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她可怜兮兮的交媾肯定没给自己带来丝毫快活,却给我们造成多大的苦难……
天使堕落
叔本华的伟大思想,同志们,是世界只不过是表象与意志。也就是说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背后,没有什么是客观的,没有Ding an sich,为了使这个表象存在,使这个表象现实,必须有一个意志;一个巨大的意志,把它强加于人。
我浪费了自己全部精力就为了这些傻瓜吗?我是为了他们活着吗?为了这些可怜虫?为了这些极端平庸的白痴?为了这些小便池边的苏格拉底吗?一想到你们我的意志就松懈了,衰退了,一蹶不振了。还有梦想,我们美好的梦想,再也得不到我的意志的支撑,就像一幢大房子断了顶梁柱一样坍塌了。
庆祝无意义
瞧瞧所有这些人!瞧!你看到的至少有一半长得丑。长得丑,这也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吗?一辈子长个丑相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没有片刻的安宁!你的性别也不是你自己选择的。还有你眼睛的颜色。你所处的世纪。你的国家。你的母亲。重要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选择的。一个人只对无关紧要的事拥有权利,为它们那就实在没有理由斗争或者写那些什么宣言了!
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这里,在这座公园里,在我们面前,您瞧,我的朋友,它就绝对明显、绝对天真、绝对美丽地存在着。是的,美丽。就像您自己说过的:完美无缺的节目——根本是无用的,孩子们笑——不用知道为什么——不美吗?呼吸吧,达德洛,我的朋友,呼吸我们周围的无意义,它是智慧的钥匙,它是好心情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