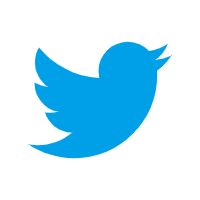南极
小时候有人告诉她,地狱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那是你可能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况。“我一直以为地狱会冷得让人受不了,在那里你会冻得半死,但你并不会完全失去意识,也不会有什么感觉,”她说,“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轮冰冷的太阳,还有魔鬼,在盯着你。”她打了个寒噤,身子颤抖了一下。
爱在高草间
“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医生的妻子说,“最可笑的是,我曾经祈祷让他离开我。我曾经双膝跪地,念一遍圣父祷文,念十遍万福马利亚,再念一遍圣三光荣经,让他离开我。他把你写的信和送的东西都藏在阁楼里;我常常听到他晚上搬梯子、爬阁楼的声音。他一定以为我是个聋子。总之,当我发现那些东西时,当他走进屋时,我确信他会离开我。有一点对你算是个安慰,他爱上了你。我敢肯定。我没有勇气离开他,他也没有勇气离开我。怎么说呢,我们都是懦夫。这真是个该死的悲剧。”
有胆量就来滑
她曾经认为他就像罗伯特·德尼罗或者肖恩·潘之类的硬汉,深沉,不显山露水。她和他一起生活了十年,试图进入他的内心,因为她认为既然他费了那么大劲,那里面一定有真正珍贵的东西,就像被困在牡蛎壳里的珍珠。但后来她放弃了,意识到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坚硬的空壳。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建造那个东西,然后进入了那种状态,完全忘记了他一开始保护的是什么。
燃烧的棕榈树
她走进屋。窗户打开了。她走出来,手里拿着她的漂亮外套、她的养老金簿,还有他母亲的结婚照。她在茅草屋里把灯油洒成一条线,然后点燃。不一会儿,客厅的窗帘就着火了。墙纸在燃烧,棕榈树在燃烧,茅草屋顶变成了火球。外婆挽着男孩的胳膊,两个人开始步行,走过了弯道。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男孩正面对着那个地方。房子的碎片,点燃的稻草屑,过去的点点滴滴,都在空中飘舞。路很黑,黑得看不见前方。走到那所旧学校时,他们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山谷里燃烧的房子。山墙一端枯死的松树在燃烧。一辆联合收割机的前灯在麦田里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