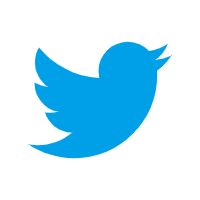航海日记
没有陆地的影子,也没有船影和云影,犹如装在巨大玻璃瓶内的海洋。这绮丽的大海,仿佛凌驾于即将看到的任何一个绮丽的神秘的国度。那时候,我们动辄想起最扫兴的事情。
北美纪行
海湾中央雨云翻滚,远方艳阳当空。对岸整个市街,既是朗朗白昼,又像溶溶月夜。进一步说,这个城市的每一座房屋,就像只有获得太阳的照射才能发光的死去的星辰,一起散放出路灯所不及的灿烂的白光。可以说这是它们由于受到超出自身能力的光照之后,储满了无力的恍惚感。
南美纪行
面包山(Sugarloaf)山峰周围的海岸线灯火辉煌,看上去宛若置于黑色大理石桌面上的项链。我深知这样的形容很凡庸,但某种瞬间薄弱而纯粹的美的印象,只能委身于凡庸的形容。美,为了不暴露自己的隐秘,只好努力与凡庸亲近。其结果,我们只能将真正的美看作凡庸,又把真正的凡庸当成美。
我想起来了,那座突然出现于梦中的都会,那座没人居住的奇怪的死城般极其错杂、美丽、静寂的都会,我曾在夏季痛苦的夜梦中经常梦见过它。都会像塔一般重叠耸立,背景鲜丽的夏日天空的颜色和云彩的颜色一样。
欧洲纪行
杂技演员向观众展示自己所追求的肉体的极限。然而,他们知道哪里是临界线,并及时返回,含笑答谢观众的喝彩。他们绝不跨越人的极限。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精神一边冒着与杂技演员同样的危险,一边毫不知情地轻易跨越人的极限。
雅典和德尔斐
天空绝妙的蓝色对于废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帕台农的圆柱之间不是这样的蓝天,而是北欧阴霾的天空,那效果恐怕就会减半。正因为效果显著,这蓝天似乎是专为废墟配备。这残酷的蓝色的静谧,仿佛预见了神庙被土耳其军队破坏的命运。
奥林匹亚废墟之美是什么类型的美呢?这废墟和断片之所以依然是美的,也许在于整体结构源于左右相对称的方法这一点上。断片容易使人窥见失却部分的构图。不论是帕台农,还是厄瑞克忒翁神庙,当我们想象失却部分的时候,不是根据直感,而是根据推理。这种想象的喜悦,比起所谓空想的诗歌来,更是悟性的陶醉。当看到这一点时我们的感动,就是看见普遍的形骸的感动。
牺牲的呼喊反响到圆柱上,那些鲜血定曾美丽地流溢在崭新而白皙的大理石面上。在希腊雕刻中,这种石头总是被用来表现人的肉体,血液和蓝天的颜色十分相似。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废墟,虽然不缺少蓝天的蓝色,但缺少同鲜血色彩的对照。随处只能依照盛开的罂粟花的殷红去想象它。
我们的苦恼必然为时间所解决,当时间解决不了时,死就会为我们解决。希腊人所具有的就是这种现世的虚无主义。希腊人对于生抱着极端的恐惧而雕刻那些苍白的石头,用那苍白的大理石制作众多的雕像,并借此将他们自己从生的可怕的痛苦中解放出来。
生反复无尽,我们死后也不能自我终止其生。我们从众多的希腊雕刻群中看到,因解放而受束缚,因自由而固守命运,被生的无尽的羁绊所捆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