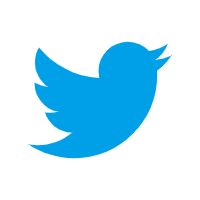Fireworks: Nine Profane Pieces
一份日本的纪念
这个国家已经将伪善发扬光大到最高层级,比方你看不出武士其实是杀人凶手,艺妓其实是妓女。这些对象是如此高妙,几乎与人间无涉,只住在一个充满象征的世界,参与各种仪式,将人生本身变成一连串堂皇姿态,荒谬却也动人。仿佛他们全都认为,只要我们够相信某样事物,那事物就会成真,结果可不是吗?他们确实够相信,而事物也成真了。
我们身旁满是稍纵即逝的动人意象,烟火、牵牛花、老人、孩童。但最动人的意象是我们在彼此眼中虚幻的倒影,映现的只有表象,在一个全心全意追求表象的城市。
刽子手的美丽女儿
葛瑞倩,山中唯一的一朵花,掀起白围裙和摇曳的条纹亚麻布裙,以免弄皱或弄脏,但即使在动作的最后关头,她父亲也不拿下面具,因为没了面具谁还认得出他?为了这地位,他付出的代价便是永远被孤独监禁在自己的权力里。
在那发臭的空地上,在他将亲生独子斩首的木墩上,他行使那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一夜,葛瑞倩在缝纫机里发现一条蛇,并且,尽管她不知道脚踏车是什么,哥哥仍踩着脚踏车在她不宁的梦境里绕圈圈,直到公鸡报晓,她出门拾蛋。
紫女士之爱
毕竟游乐场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也许每一处游乐场都只是某个单一、庞大、最初的游乐场的零星碎片,在很久以前惊异世界的一场不明的颠沛流离中散落各地。不管在哪里,游乐场都保有它那不变、一致的氛围。旋转木马像西洋棋的国王那样象形,绕着如星球轨迹般不变的圆圈,也如星球般与此时此刻的寒酸世界毫无关联,任这世界的囚徒来目瞪口呆看着如此免于现实的特殊自由。
主人
他那把来复枪最爱单挑的是丝般冷漠平滑的大猫,最后更特别专精于扑杀毛皮有花纹的那些,如花豹、猞猁。是不承认人心中有任何神性的缄默诸神指尖沾着棕色墨汁,在那些动物的毛皮上印下条纹斑点的语言,死亡的象形文字。
The Bloody Chamber and Other Stories
老虎新娘
若四周这整片蛮荒孤寂中看不见任何其他人,那么我们六个——包括骑士与坐骑——全加起来也没有半个灵魂,因为世上所有高等宗教一律明确宣言:野兽和女人都没有那种虚无飘渺的东西,上帝打开了伊甸园的大门,让夏娃和她的魔宠全数跌出。
Black Venus
黑色维纳斯
悲哀,多么悲哀,晚秋时节这些烟蒙粉红、烟蒙紫褐的傍晚,悲哀得足以刺穿人心。太阳在层层俗艳的卷云中离开天空,苦痛进入城市,一种最为苦涩的悔憾,一种对从不曾得知的事物的怀旧,这是岁末的苦痛,充满无能渴望的时光,无法慰藉的季节。
吻
每个城市都自有其内在逻辑。想象一个城市用孩童的蜡笔画成直截了当的几何图形,有赭,有白,有浅赤褐;房舍的淡黄色低矮露台仿佛从泛白泛粉红的土地长出,而非建造于其上。一切都罩着薄薄一层尘沙,就像蜡笔留在你手指上的碎粉。
大屠杀圣母
这村里没有任何东西会激起我以往贪婪的热情;要是我肚子饿,有需要,印第安人土地上任何一个锅里的食物我都可以吃,因为习俗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欲望和需要都不能让我做贼。
厨房的小孩
事实上,厨房不正有些神圣吗?那些被煤灰染黑的石拱顶高高在我头上,挂着火腿和一串串洋葱、一束束干燥香草,看来有点像老教堂走道上方垂挂的教团旗帜。摸来冷凉、发出回音的石板地由善男信女每天两次跪着擦洗得一干二净,一排排刷洗得发亮的金属器皿挂在钩子或栖在架子上,静待需要的时机到来,就像许许多多圣餐杯等着食物圣礼。而炉灶就像祭坛,是的,祭坛,我母亲永远在坛前垂首致敬,唇上一层薄汗,火光映红双颊。
秋河利斧杀人案
看见老波登沿街朝你走来,你会本能地对人必有死的此项事实充满敬意,他似乎就是死亡的瘦削大使。你也会想到,当初我们直立起身,以双腿而非四腿行走,是何等战胜自然的一大胜利!因为他把自己挺得直直,充满沉重决心,看见他走路的人永远会想起直立行走是不自然的,是战胜地心引力的,本身就是精神超越物质的超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