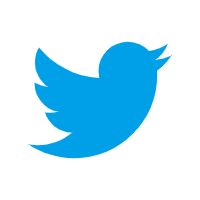我之前从没有见过这样一种东西,竟能在同一时间内传递出这么多预示着愤怒与毁灭意愿的信号。它的脸,它的角,它那双注视着我们的冷眼——一切在我的脑中唤起的全都是恐惧,而我能感受到的还不止这些——我还感受到了一样更陌生、更深层的东西。那一刻,我感觉仿佛是有人犯下了一个大错,竟然允许那个生物站在太阳的图案里—这头公牛理应被深埋在地下的泥土与黑暗之中,让它出现在草地上只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就在我穿过一个格外不友好的方格时,我听到四周响起了某只动物痛苦的哀号声,一幅画面随即闪入我的脑海:罗莎,坐在野外某处粗糙不平的地里,身边散落着细小的金属碎片,一面伸出双手,抓住自己的一条僵挺在眼前的大腿。这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只停留了一秒,可那只动物却还在叫个不停,我感觉地面正在我的脚下崩塌。
我想,我之所以恨卡帕尔迪,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怀疑他也许是对的。怀疑他的主张是正确的。怀疑如今科学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我女儿身上没有任何独一无二的东西,任何我们的现代工具无法发掘、复制、转移的东西。古往今来,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人们彼此陪伴,共同生活,爱着彼此,恨着彼此,却全都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一种我们过去在懵懵懂懂之中一直固守的迷信。
但我其实并不对我们的现状感到愤怒。如果一个孩子比另一个孩子能力更强,那么机会理应留给那个聪明的孩子。还有责任。我接受这一点。但我不能接受的是,里克没法儿过上体面的生活。我拒绝接受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如此残酷。里克没有接受过提升,但他依然可以拥有远大的前程,成就了不起的事业。
有人在用力拉我的胳膊;但此刻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如此之多的碎片,仿佛一堵坚实的墙。同时我开始怀疑,许多碎片其实都不是三维的,而是利用巧妙的明暗技法画在平面上的,给人以一种浑圆饱满、有进深感的假象。
我不禁寻思,不知当年的海伦小姐和万斯先生对待彼此是否也像如今的乔西和里克这样。也不知将来有一天,乔西和里克会不会也用那样的冷酷彼此相向。我又想起了父亲在车里谈到人心,谈到它是如何的复杂,我又看到了他站在院子里,就站在低垂的太阳面前,他的身形和他傍晚的黑影交织融合成一个细长的形状,与此同时他的手伸向上方,从库廷斯机器的喷嘴上面拧下保护盖,而我则焦急地站在他的身后,手里拿着那只塑料矿泉水瓶,瓶子里面装着那珍贵的溶液。
我不需要思考。乔西和我一起长大,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而且我们还有我们的计划。所以,我们的爱当然是发自内心,直到永远的。至于谁接受过提升,谁没有接受,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这就是你要的答案,克拉拉,也是唯一的答案。
我想我要说的是,在某种层面上,乔西和我永远都会在一起——某种深度的层面上,哪怕我们踏进了外面的世界,从此再不相见。这话我不能替她说。但一旦我踏进了外面的世界,我知道我永远都会继续寻找着一个就像她那样的人。至少是像那个我曾经认识的乔西。所以那从来都不是欺骗,克拉拉。不管你当年是和谁达成的约定,如果他们能径直看透我的内心,看透乔西的内心,他们会明白你没想要骗他们的。
她的步态还是那样的小心翼翼,从来都没有变过,这使得她的双脚每走一步,都会咯吱咯吱地陷入碎石之中。她看上去兴奋又健壮,就在她的手触到我的前一刻,她高举起双臂,仿佛是要尽她的所能,摆出一个最大的Y字来。接着她就将我揽入了怀抱,许久都没有放手。她个头已经比我高了,因此她只能稍许蹲下,下巴枕在我的左肩上,她浓密的长发遮住了我的一部分视野。等到她抽身与我分开时,她的脸上挂着微笑,但我也看出了几分悲伤。
卡帕尔迪先生相信乔西的内心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是无法延续的。他对母亲说,他找啊找,可就是找不到那样特别的东西。但如今我相信,他是找错了地方。那里真有一样非常特别的东西,但不是在乔西的心里面,而是在那些爱她的人的心里面。
太阳对我非常的仁慈。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对我很仁慈。不过在我陪伴乔西的时候,有一回,他格外的仁慈。我想要让经理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