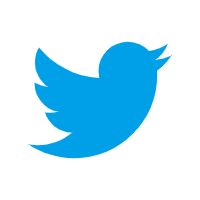发端
我们称之为思想的这种东西,不是事前产生的,而是事后产生的。思想一般作为因偶然冲动而犯罪的人的辩护者身份出场。辩护人赋予其行为某种意义和理论,以必然替代偶然,以意志置换冲动。思想虽然不能给撞在电线杆上的盲人治伤,但至少有能力证明受伤的缘由不是因为盲目,而是因为电线杆子。每一个行为都跟着一个事后的理论,于是理论成为体系,而人——行为的主体却明显地变成了行为的可能性。他具有思想。他将纸屑扔到大街上。他是因思想而将纸屑扔到大街上的。这样一来,思想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无限扩大范围,而思想持有者就成了思想牢笼里的囚犯。
他把珍藏的河内若女能面盖在死者的脸上。他的动作像用力扣上去的,所以死者的脸犹如熟透胀裂的水果,被面具压碎了。——俊辅的这个行动谁也没注意,不到一小时,尸体就被烈火包围,烧得无影无踪了。
通往康子那座城镇的公路,数度靠近海面。从悬崖上可以俯瞰夏季海上的火光。那不太明亮的火焰在水面上燃烧,大海泛着沉静的痛苦,那是一种被雕镂的贵金属般的痛苦。
镜中的契约
他们两个互相假装入睡以欺瞒对方,结果各自都受到蒙骗而堕入困倦。他做了一个幸福的梦,梦见神允许天使将他杀掉。他哭了,哭声和眼泪都没有泄漏到现实世界。因而,悠一感到自己依然残留着浓重的虚荣心,他放心了。
康子感到洗过的头发迅速变得干爽、清凉起来。粘在太阳穴附近的几根头发,摸上去像草叶一样冰冷,仿佛不是自己的头发。她害怕用手摸自己的头发,这逐渐干燥的头发,其手感里包含着爽净的死。
孝子的婚事
悠一头靠在座席背上,稍微拉开些距离,瞧着康子低俯的脸庞。能否看作男孩子的脸呢?那眉毛?眼睛?鼻子?嘴唇?他像画坏了几幅素描的画家一样咂着舌头。他终于闭上眼睛,一心把康子想象成一个男人。然而,这种极不道德的想象力,使得眼前这位美丽的少女,变成比女人更难去爱,或者说越来越像一个不可爱的丑恶的影子了。
济度开始
俊辅发现自己唯一的收藏品——数万册辉煌的图书,似乎立即羞得面孔通红。在生命面前,在这光耀的肉的艺术品面前,众多的书籍皆为自己虚伪的装潢而羞耻。他的全集的精装本,三面金箔虽然没有失去光泽,但集中涂抹在裁断的高级纸张上的金箔,几乎都映照着人的面影。当青年取出全集中的一册书时,俊辅似乎觉得蓄集在书页之中的青春的影像,净化了这些藏书的尸臭。
女人们的不如意
康子的父亲在百货店采购部能买到廉价的进口衣料,她很早就为这次秋季的晚会定做了服装。晚礼服是象牙黄的波纹绸。宽阔的裙裾展开来,充分显现了波纹绸严冷的量感,那些流光溢彩的纹络,眯缝着沉静而死寂的纤细的眼眸。胸前装饰着一轮卡特来兰,薄紫的花蕊围绕一圈仄黄、淡红或纯紫的花瓣儿,尤其突显了兰科植物所特具的那种妩媚、娇羞的魅力。颈项上戴着黄金锁子串连的印度产小坚果的颈饰。从那深深隐藏于肘间的青蓝色的手袋里,以及胸前的卡特来兰上,弥散出雨后空气般爽净的香水味儿。
从窗外看到别人的不幸,比起在窗内看到的更加美丽。这是因为,不幸很少能越过窗棂扑向我们……音乐的专制支配着集合的人群,这是秩序在起作用。音乐以类似深深疲劳的感情驱动着孜孜不倦的人们。俊辅想,音乐的旋律流动之中,音乐也有一个不可侵犯的真空的窗户,自己正在透过这个窗户望着康子和镝木夫人。
嫉妒
然而,美使人沉默这一信仰,不知不觉已经化为过去的东西。美不再使人沉默,即使美从盛宴中走过,人们也不会停止喧哗。去京都的人,总要看看龙安寺的石庭,那院子绝不难解,只是一种普通的美,一座使人沉默的院子。但滑稽的是,拜谒石庭的现代人,并不仅仅满足于沉默。他们总想说点儿什么,于是紧蹙眉头,硬诌出几首俳句来。美似乎逼使人饶舌。人们每当面临美,就急不可待地阐述感想,觉得这是义务,感到美必须迅速折价变卖,不折价就有危险。美仿佛是炸弹,是产生一切困难的根源。这样一来,我们就失掉以沉默保有美的能力,失掉为之献身的崇高的能力。
家常便饭
艺术作品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具有坚强的生的意志,这不正是死的感动所致吗?俊辅的东方式梦想动辄倾向于死。在东方,死较之生具有数倍的活力。俊辅所考虑的艺术作品,就是一种精练的死,是使生接触先验之物的唯一的力量。
“我想转变,我要变成一个现实的存在!”
俊辅倾听着。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他的艺术作品发出的悲叹之声。悠一神色悒郁,又加了一句:
“我对秘密的存在已经厌倦。”
……此时,俊辅的作品第一次开口说话了。从青年激烈而美丽的声音里,俊辅仿佛听到了镌刻完成的巨大名钟的音律,这音律满含着造钟人疲惫不堪的怨艾。
无计可施的星期日
剧场、咖啡馆、动物园、游乐场、大街、郊外,到处都是“多数决定原理” 在高视阔步。老年夫妇、中年夫妇、青年夫妇、情侣、家庭、小孩、小孩、小孩、小孩、小孩,还有那该死的童车队列,一边欢呼,一边前进。悠一要想学他们,同康子一起逛马路,那也很容易办到。无奈头顶上苍天有灵,一眼就能识别真假。
旅行前后
自然与艺术作品之间,有着媚俗的隐秘的叛逆之心。艺术作品对自然的谋叛,犹如卖笑女子精神的不贞,阴柔而深切的虚伪,多以媚态的形式,装出一副力图依偎自然而原封不动摹写自然的样子。然而,没有比寻求自然近似值的精神更具人工化的精神了。
妻祸即夫祸
悠一在大街的一角叫住一辆出租车,他的身影显得很小。车子开走了,镝木伯爵想一个人走到天亮。他在心里没有呼唤悠一的名字,而是呼唤着夫人的名字,只有她才是他的伙伴。她既然是他恶行的伙伴,也就是他灾祸、绝望和悲叹的伙伴。他决定一个人去京都。
日渐成熟
小小的光洁的脚骨,布满皱褶的清净而光亮的足底,从深夜里伸出来踢蹬着黑暗,每当她想象着这样的情景,觉得自己的存在就是那温热的、充满养分的、鲜血模糊的、黝黑的肉块。这是一种被腐蚀的感觉,是从内部受到深刻侵犯的感觉,是受到最为沉重的强奸的感觉,是疾病的感觉,死亡的感觉……任何不伦的欲望和肉感的恣意,在这里都能得到体面的宽宥。
对话
穿过湿漉漉的景色颓丧的灰色楼群街道,代之而来的是工业街阴霾而昏黑的风景。湿地和荒芜的狭窄草地的对过,有一家镶满玻璃的工厂,坏了几块玻璃,煤烟熏染得黑漆漆的屋里,大白天也亮着许多裸露的电灯泡,点点可见……电车有时经过高台上古老的木造小学校,U字形校舍空荡荡的窗户面向着这边。雨湿的校园看不见一个学生,只有油漆斑驳的肋木架伫立着……
转变
这时,悠一看看痛苦至极的妻子的脸,又看看曾经被他当作万恶之源的那个部分,正在如火一般鲜红,他的心改变了。悠一那为所有男女赞叹、仿佛只为供人观赏而存在的美貌,开始恢复本身的机能,眼下只为观看而存在了。那喀索斯忘记了自己的脸孔。他的眼睛向着镜子以外的对象。他曾经直视过酷烈的丑恶,这和观察他自身是一样的。
以往悠一存在的意识,无一不是“被人观看”。他感到自己存在,就是因为他感到被人观看。即使不为人观看,自己也确实存在着,这种全新的存在意识使得这个年轻人陶醉了。就是说他自身也在观看。
一醉醒来是夏天
对于民众欲望的再发现,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打算通过各自不同的形式加以实现,前者试图将类似人造兴奋剂的哲学作为火种,重新燃起市民阶级衰弱的欲望,唤醒他们集结起来。纳粹主义最理解什么是衰弱。悠一不能不从包括人工神话、隐蔽的男色原理、美青年组成的党卫军以及美少年组成的希特勒少年队等组织之中,寻求有关这种衰弱的该博的知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则着眼于残留在衰弱欲望底层的一元化的被动欲望,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激化起来的矛盾引起贫困的新的强烈欲望。
此时,西边天空,云朵庄严灿烂,数条金光刺破云层,像一幅古战场的绘画,将光芒的末端射向这边。于是,在不爱亲近自然、单凭丰富想象的俊辅的眼里,那湛蓝色的波涛涌动的海面出现了幻景,看上去仿佛累累死尸。
古代斯巴达为了训练少年们战斗时的敏捷,机灵的盗窃行为不受惩罚。一个少年偷了一只狐狸,但因失败而遭到逮捕。他把狐狸藏在衣服里头,否认犯罪。狐狸撕裂了少年的肚肠,他依然矢口否认,没有喊一声疼痛就死了。这个故事之所以传为美谈,或许说明了克己比盗窃更符合道德,可以偿还一切。但事情并非如此。他害怕的是暴露致使非凡的恶行堕落为凡庸的犯罪,他是因羞耻而死去的。斯巴达人的道德观是古希腊不可遗漏的审美意识,精妙的恶较之粗劣的善,因美丽而富于道德性。
精神及金钱诸问题
康子微笑了。微笑里含着严冷的漠不关心。悠一很是尴尬,面颊羞愧地发红了。不久,这位不幸的青年说出了下面一段台词。他的话很可能被一眼看穿是充满戏剧性的轻薄的自白,但同时也是他出生以来对女人说出的最深情、最诚实的自白。
“旅行途中,我想念的只有你一人。这段时期,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切实感到,我最喜欢的依然是你。”
康子镇定自若。她轻轻一笑,一副无所谓的神色。悠一的话仿佛是另一个星球上的语言,康子似乎隔着厚厚的玻璃墙,只是眼望着悠一的嘴唇在翕动。总之,他们已经言语不通了。
桧俊辅的“桧俊辅论”
他认为,所谓思想这种东西,像黑痣一样产生于偶然的原因,因同外界的反应而必然化,并不具备自身的力量。思想是一种过失,可以说是生来就有的过失,不可能先有抽象的思想,而后再加以肉体化,思想从一开始就是一些夸张的样式。长着大鼻子的人,他就是大鼻子思想的主人。一个耳朵能动的人,无论如何翻来调去,他都是能动的耳朵的独创思想的主人。他的所谓形式,可以说几乎都是肉体,桧俊辅立志创作类似肉体存在的艺术作品,形成讽刺的是,他的作品无一不发散着尸臭,其构造就像精巧的黄金棺材一样,给人以极端人工化的印象。
就像重大的事件必须立即加以历史的记述一样,寄寓于宝贵的美丽肉体中的青春,旁边必须有个记述者。行为和记述,同一个人绝不能兼而有之。肉体之后萌发的精神,行为之后萌发的记忆,以及仅仅有赖于此的青春的回想录,无论多么美丽,都是徒劳又徒劳的东西。
青春的一滴水,必须立即结晶,成为不死的水晶。沙钟上半部分漏下来的沙子,将近完了的时候,下半部分就会堆起同样形状的沙子,和原来的上半部分一样。青春即将终了时,漏刻一滴一滴全部结晶,旁边必须迅速刻上不死的像。
造物主的恶意,不让完全的青春和完全的精神在同一年龄上相遇,总是使青春芬芳的肉体包容着半生不熟的精神,对此不必引起慨叹。所谓青春,是精神的对立概念。不论精神如何永生,都只能是笨拙地在青春肉体精妙的轮廓上描摹一次而已。青春无意义地活着,这是莫大的浪费,是不思收获的一个时期。生的破坏力和生的创造力于无意识之中保持至高无上的均衡。必须造就这样的均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