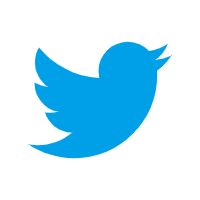时隔七年,博主重读《丰饶之海》。
一
妃殿下并非明显地回头观望,她依然亭亭玉立,只是稍许侧过脸来,掠过一丝微笑而已。这当儿,几丝鬓发轻轻飘过直立的雪白的面颊,细长的眼角里黝黑的眸子,倏忽点亮一星火焰般的微笑,端正的鼻官无意中显得清净又挺秀……妃殿下一瞬间的侧影,犹如微微倾斜的某种清净的结晶的断面,玲珑剔透,又像刹那间一闪即逝的彩虹。
二
抑或清显和本多本是同根生的植物,各自长出了完全不同的花和叶。清显毫无防备地暴露着自己的资质,一副易于受伤的裸体含蕴着尚未足以左右本人行动动机的官能,宛若一只沐浴着初春雨水的小狗,眼睛和鼻子都沾满淋漓的水滴。同他相反,本多打从人生的第一步起,就觉察到世情险恶,他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将身子团缩于屋檐下,以便躲避过分明亮的雨水。
三
那条狗定是有了伤病,到水源喝水,失足淹死了,尸首被冲下来,卡在瀑布出口的岩石上。本多被聪子的勇气感动了,同时眼前又仿佛看到瀑布出口湛蓝的天空飘浮着淡淡云彩;看到凭空悬挂的沐浴着清冽的水花的黑狗,那濡湿的闪光的狗毛,以及张开着嘴巴的纯白的牙齿和黑红的口腔。
四
门迹讲经时提到古代唐朝的元晓,他在名山高岳之间求佛问法,有一次于日暮之后,野宿于荒冢之地。夜半梦醒,口干舌燥,伸手从身边的洞穴里掬水而饮之。他从来没有喝过这样清冽、冰冷而甘甜的水。他又睡着了,早晨醒来,曙光照耀着夜里饮水的地方,没想到,那竟是髑髅里的积水。元晓一阵恶心,他呕吐了。然而,他因此而悟出一条真理:心生则生种种法,心灭则与髑髅无异。
五
然而,清显害怕仰望天上真实的月亮。他只看着那个圆水盆里早已深深印入自己心底的、金色贝壳似的月亮。终于,他的内心捕获了一个天体。他的灵魂的捕虫网,网住一只金光闪闪的蝴蝶。
但是,这面灵魂的捕网网眼粗大,一度捕到的蝴蝶,会不会又立即飞走呢?十五岁的他,却及早地害怕丧失。一旦得到又害怕丧失,这种心情成为这位少年性格的特征。既然获得月亮,今后如果住在没有月亮的世界,那是多么令人恐怖的事情。尽管他憎恨那月亮……
七
西洋法的定言命令,永远服从人的理性,但《摩奴法典》将理性无法测知的宇宙法则——“轮回”,作为自然而然的道理深入浅出地提示出来了。
“行为产生于身体、语言和意义,也产生善或恶的结果。
“心于现世同肉体相关联,有善、中、恶之别。
“人以心之结果为心,语之结果为语,身体行为之结果受之为身体。
“人因身体行为之错误,来世变为树草;语之错误,变为鸟兽;心之错误生为低等阶级。
“对于一切生物保有语、意、身三重抑制,又能完全抑制爱欲、瞋恚的人,可获得成就亦即究极之解脱。”
房子的眼眸呢?
她因为斜斜地俯着脸,他看到就在眼皮底下,自己的膝盖上,滴溜溜圆睁着一双易受伤害的小巧的黑眸子。那就像一对临时停飞的极其轻盈的蝴蝶。忽闪着的修长的睫毛,是不住扇动的蝶翅,那瞳孔是翅膀上奇妙的斑纹……
那双眼睛是那么缺乏诚实,如此接近又那么淡漠,那是随时展翅飞翔的不安和浮动,犹如水平计中的气泡,由倾斜变为平衡,由涣散到集中,无休止地来来往往。繁邦从未见过这样的眼睛。
十二
一方小小晦暗的空间的摇动,使他的思绪四处飞散开来,他即使将视线从聪子身上移开,除了明亮的小窗赛璐珞上粘满微黄的雪片之外,就再也没有值得一瞧的地方了。他终于把手伸向小毯子下面,聪子的手早已等在那里,那是守在温暖巢穴中的狡黠的手。
一片雪花飞进来,粘在清显的眉毛上,聪子看见“哎呀”叫了一声。清显不由得转过脸望望聪子,感觉到自己眼皮上一阵冰凉。聪子迅速闭上眼睛,清显直视着她紧闭双眼的面庞,只有绯红的嘴唇略显黯淡,脸蛋宛若指甲弹拨的花朵,轮廓缭乱地摇动着。
清显的心剧烈跳动,他切实地感到制服高耸的领口紧紧束缚了脖颈。聪子那张双目紧闭、娴静而白皙的面孔是个最为难解的谜。
十三
你想想看,再过十年,人们将会把你同你最鄙视的那帮家伙一样对待,你又将如何呢?那些人粗劣的头脑,用文弱的言辞辱骂他人的褊狭的心胸,欺负低年级学生,对乃木将军疯狂的崇拜,每天打扫明治天皇手植的杨桐树周围,那副感到欣喜异常的神经……所有这些东西,都将和你的感情生活混为一谈,笼而统之地处理。
历史有意志吗?将历史拟人化总是危险的。照我的想法,同我的所谓意志毫无关系。因此,这种绝非产生于某种意志的结果,也决不可以称作‘成就’。其证据是,历史所假设的成就,在下一瞬间早已开始崩溃
历史一直在崩溃,又是为了准备下一个徒然的结晶。历史的形成和崩溃,似乎只具有同样的意义。
西洋的意志哲学必须承认‘偶然’才能成立。所谓偶然,就是意志的最后避难所,一笔赌注的胜负……没有这个,西洋人就无法说明意志反复的挫折和失败。这种偶然,这笔赌注,我以为就是西洋的神的本质。意志哲学最后的避难所,如果是偶然之神,同时也只能是偶然之神,才能鼓舞人们的意志。
但是,假如偶然这东西全被否定了,又怎么办呢?任何胜利、任何失败之中,完全没有偶然的用武之地,又怎么办呢?要是这样,一切自由意志的避难所都没有了。偶然不存在的地方,意志就会失掉支撑自己本体的支柱。
十四
赶庙会一般华丽、热闹的场景,突然从眼前一掠而过。黑暗之中,一切幻象连同那乙炔灯强烈的光芒和乙炔的臭味,以及气球、风车和五颜六色的小糖人耀眼的光彩,一起消失了。
……她在黑暗里睁开了眼。
“干吗这样瞪着眼睛?”
饭沼带着不耐烦的语气问道。
一群老鼠又在天花板上跑动起来,声音细碎而急促。群鼠一阵闹腾,仿佛从广大无边的黑暗旷野的一个角落跑向另一个角落。
十五
每当想起下雪的早晨,第二天即便是晴天丽日,我的胸间也会继续飞降着幸福的雪花。那片片飞雪映照着清少爷您的面影,我为了想您,巴不得住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下雪的国度里。
我最高兴的是,清少爷您有一副美好的心灵。您一眼看出我任性的心底里,隐含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温情,毫无怨言地带我去赏雪,使得我心中最叫人羞惭的梦想实现了。
清少爷穿着一身严整的制服,威风凛凛,正是使我着迷的雪的精灵,我真想融入清少爷美丽的身影,同白雪化为一体,即使冻死,也是无比幸福的。
十七
聪子从湖水方向转过身子,脸孔没有直接看着这边的窗户,只是高高兴兴朝着主楼走来。这时,清显想起幼年捧裾的时候,春日宫妃的侧影没有完全转向后边,自己未能尽情一睹芳颜,六年之后,这种遗憾今天才得到治愈,宛若长久的渴望实现于一瞬之间。
这好比时间结晶体的美丽断面变换了角度,隔了六年又在他眼里散射着无上诱人的绚丽的光彩。他看到聪子站在春阳阴翳的光影中,一副缥缈的冁然而笑的体态,紧接着又迅即抬起洁白的纤腕,弯成弓形,捂住了自己的芳唇。她那婀娜的腰肢,仿佛鸣奏着一曲弦乐。
十八
这些女人秋波流慧,顾盼欢然,但她们的眼神是独立的,就像嗡嗡嘤嘤的羽虫可厌地飞旋、萦绕,而这些决然不含蕴于聪子所具有的优雅的眼波之中。
他远远望见正在同洞院宫说话的聪子,她的侧影映着迷离的夕阳,宛如遥远的水晶、遥远的琴音、遥远的山间襞褶,充溢着距离所酿造的幽玄,而且,在以暮色渐浓的树林间的天空衬托下,好似黄昏里的富士山一样轮廓鲜明。
二十二
绿叶簇簇,喷薄而出,山山岭岭,从嫩黄到墨绿,千种绿色如波涛奔涌,尤其是透着深红色彩的小枫树的树荫,看起来就像是一块铺着紫金的地面。
“哎呀,灰尘……”
母亲忽然注视着聪子的面颊,正要用手帕擦拭的时候,聪子立即缩了缩身子,沾在脸上的灰尘骤然消逝了。母亲这才发觉,那是玻璃窗上的一块污垢搪住了日光,将影子映射到聪子的脸庞上了。
二十四
清显透过头发空隙,望着她那可爱的全神贯注的侧影。聪子咬着下唇,小巧、伶俐的牙齿闪现着光亮,虽然还是幼女,但鼻官秀挺、端丽、匀称,她的那副长相使得清显总也看不够。还有那沉郁而黯淡的墨香,纸上走笔时风翻竹叶般的沙沙声响,砚台上“砚海”和“砚岗”奇怪的名称,自那不起一片浪花的海岸陡然凹陷的墨海,深不见底,浓黑的积淀,墨上的金箔剥落,飘散下来,犹如光闪闪的月影浮泛于永恒的夜的海面……
在这剩下的一天,清显任想象的翅膀自由翱翔,对外界的一切一概不放在眼里,往昔沉静而明晰的镜子已经粉碎,热风扑打着心扉,喧骚不止。过去,他些微的热情必然伴有的忧郁的影子,如今在这激烈的热情里再也找不到一鳞片爪了。要举出与此相似的感情,那首先只能提到最为接近的“欢喜”了。然而,在人们的感情中,没有比毫无理由的激烈的欢喜更加阴森可怖了。
两人玩双六棋,聪子赢了,她的小小牙齿咬着皇后赏赐的手工制作的点心,一边菊花瓣上的红色鲜艳了,消融了,接着,白菊冷峭的雕刻的棱角随着舌尖的触及,化作甘甜的浆,飘散着香味……一栋栋幽暗的房舍,从京都带来的古代皇宫风格的秋草画屏,还有那岑寂的夜晚,以及聪子黑发底下娇小的哈欠……
二十六
清显透过布幔望着外面,渐渐倾斜的夏阳宛如浓稠的果汁,浸泡着林子里枝叶繁茂的树梢,明光闪烁。鸟居坂附近一棵巨大的橡树,嫩绿的树冠越过高高的红砖围墙,好似白色的鸟巢,缀满了众多略带红晕的白花。
二十七
清显依旧一声不吭地打量着聪子,她坐在对面,装束齐整,毫发不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聪子蓦然抬起头来,同清显的目光碰到一起,刹那之间,迅即闪过一丝清炯而犀利的光辉,清显知道聪子决心已定。
“信不能还,因为还要再见面的。”
一刹那,清显鼓足勇气说。
“哎呀,少爷。”
蓼科的声音含着愠怒。
“您怎么能像个孩子一样,说话不算数呢?……您想过没有,这样做是多么可怕,毁掉的可不光是我蓼科一个人哪!”
“算了,蓼科,要请清少爷尽早还信,那就只能再见一次面了。这是解救你和我唯一的一条路,如果你真的也想救我的话。”
聪子制止了蓼科,她清亮的声音仿佛来自别一种世界,清显听了也感到一阵战栗。
二十九
本多希望自己的理性永远成为那灿烂的光亮,但他难于舍弃为热烈的黑暗所吸引的心性。然而,这热烈的黑暗只是一种魅惑,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是确确实实的魅惑。清显也是魅惑。而且,这种从根本上摇撼生命的魅惑,实际并非属于生命,而是关联着命运。
三十二
置身于大海和陆地如此壮大的分界线上,宛若站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一瞬之间见证了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移转,此时的心境难道不是如此吗?本多和清显生活着的现代,也不外乎相当于一次潮涨潮退时的境界罢了。
……大海就在眼前完结了。
遥望远洋的波涛,就会明白,它们是经过多么漫长的努力,最后才不得不在这里宣告完结。于是,全世界所有海洋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企图,终于徒劳地结束了。
退去的远方的波涛,同一道道奔涌而来的波浪相重叠,没有一道波浪背对着海岸,而是混成一体,一同咬紧牙关指向这里。可是向洋面望去,刚才岸渚上看似强劲的波浪,实际上呈现出稀薄而衰退的气象扩散开去。渐渐地,渐渐地流向远洋,海水变浓了,岸边海水稀薄的成分渐渐地被浓缩,被压挤,以致使水平线变成深绿色,无边的浓缩的青碧就会结成坚硬的晶体。虽然装点着距离和间隔,但唯有这种结晶才是海的本质。这种稀薄、慌乱的波的重复,最后凝结成的蓝色的晶体,那才叫大海呢……
三十三
我们活着,却具有丰富的死,葬仪、墓地、供在那里枯萎的花束、对死者的记忆,还有当前的亲友的死,接着对于自己的死的预测。
的确有一种思维,不把人作为个体,而是当作一条生命的河流看待。不认为是静止的存在,而作为流动的存在。正像当时王子所言,一种思想为各个“生命的河流”所继承,同一种“生命的河流”为各个思想所继承,这两者是一样的道理。因为生命和思想同化为一体了。而且,这种生命和思想本为同一体的哲学一旦推广开去,那么,统括无数生命之河的生命大潮的连环,人们称之为“轮回”的东西,也就有了成为一种思想的可能……
这座沙子伽蓝该点灯了。好容易精雕细镂的寺门前观和纵长的窗户,已经均匀地弥漫着暮色,连轮廓都变得一团昏黑,细碎的水花似濒死者喑弱的白眼,这个世界难以消亡的余光被搜集起来,以这种聚合而成的白色为背景,寺院渐渐化为朦胧的暗影。
三十七
面对这个比亲骨肉还要疼爱的姑娘,蓼科和聪子接触并没有感到自己怀着真正的悲哀。这种爱护和悲悯之间隔着一道栅栏,蓼科对聪子越是疼爱,就越是希望聪子和自己一起共享莫名的可怖的欢乐,那是隐藏在可怖的决断之后的欢乐!一种骇人听闻的罪愆,要通过所犯的别的罪愆获得救赎,到头来两罪相抵,二者均不复存在。一种黑暗,掺和进别一种黑暗,就会招来艳丽的曙光,而且都在隐秘之中!
三十八
如今,清显所怀有的是一种真正的感情。比起他曾想象的一切恋爱的感情,这种感情粗杂、无趣、荒寂、幽暗,远离一切都雅,无论如何都不能写入和歌。他第一次保有这般丑陋的素材。
四十一
他的祖先没有对凌辱表露过微笑,而是稍许展现优雅的权威以示抗争。然而现在,家传的踢鞠废绝了,吸引世俗人等的诱饵没有了。真正的贵族,真正的优雅,并不想给他些微的伤害,对于充满善意的赝品无意识的凌辱,只能报以暧昧的微笑。面对新的权力和金钱,文化所浮泛的微笑里,闪烁着极其纤弱的神秘。
四十二
似乎很自然地轮到聪子了,他对她说:“好了,多保重。”
他的话带着轻快的调子,同时伴随着轻快的动作,这时,似乎伸手搭在聪子的肩膀上也有可能。但是,他的手麻痹了,不能动弹了。因为这时候,清显看到聪子正直视着自己。
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看上去潮润润的,然而那种莹润似乎和清显所畏惧的泪水依然相距遥远。眼泪硬是被强忍住了。那是一位溺水之人径直向他投射过来的渴望救助的眼神啊!清显不由怯懦了。聪子修长俊美的睫毛,犹如一朵蓓蕾猝然绽开,向外部世界尽情展现着妍丽的鲜花!
“清少爷,您也多保重……祝您愉快。”
聪子一口端正的语调。
四十三
灿烂的秋阳照耀着柿子,一根小枝条上结了一对柿子,其中一个柿子漆黑的影子遮盖在另一个柿子上。有一棵柿树,所有的枝条都密密麻麻缀满了鲜红的柿子。果实和花不同,只有残留的枯叶随风微微飘动,而果实却不为风力所动。因此,抛撒在半空里的众多柿子,犹如被钉子牢牢钉住一样,镶嵌于寂然不动的苍穹。
四十四
“你削掉头发啦?”
夫人一把搂住女儿的身子。
“妈妈,我已经无路可走了。”
聪子这才第一次正视着母亲,一双眸子摇曳着蜡烛小小的火焰,眼角里辉映着银白的曙光。夫人从未见过女儿眼中射出的可怖的曙光。聪子手里一颗颗佛珠也含蕴着一样的白色光亮。这一串意志达于极致而丧失意志的冰冷的佛珠,一起渗出黎明的曙色。
四十五
人人心里都在描绘聪子应该佩戴的假发,它比真发还要光洁、流丽,如射干果一般乌黑闪亮。它就是强加授予的王权。浮泛于宇宙中梦幻般黝黑的发型,散射着耀眼的光芒。它是浮游在白昼光海之中的夜的精髓……假发下面应该嵌入一副美艳而悲凉的脸庞,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四个人虽说都想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仔细考虑。
四十六
随着一绺绺头发掉落下来,聪子的脑袋有生第一次感到如此清凛的寒凉。自己和宇宙之间夹持着的那层燠热的充满阴郁烦恼的黑发剃掉了!从此,头盖骨周围展开一片谁也未曾触摸过的新鲜、寒冷而清净的世界。剃去的部分逐渐扩大,冰冷的头皮也随之扩大,犹如涂上一层薄荷。
头上凛冽的寒气,好比月亮那样死寂的天体径直毗连着宇宙浩渺的空气,其感觉或许就是如此吧?头发似乎就是现世本身,渐渐颓落,颓落下去,变得无限遥远。
五十
他心中每每描画着这样的景象:一只鳖鱼从黝黑的湖水中悄然露出头来向他窥望。那鳖鱼埋身于湖底温热的淤泥,时时冲破腐蚀时光的梦境和恶意的水藻,从半透明的湖水中浮出身子,长年累月凝视着清显的成长。如今,这道诅咒突然解除了,鳖鱼被宰杀,他于不知不觉之间喝下鳖鱼的鲜血。因而,一件事情蓦然了结了。恐怖柔顺地进入清显的胃袋,开始转化为一种不可预测的活力。
五十一
过去,他也和别人一样向往过西洋,如今他却执着于日本最纤细、最美丽的一点。然而,打开世界地图,广漠的海外诸国自不必说,即使染成红色的小虾一般的日本也显得那么俗恶不堪,他心目中的日本,原是一个蔚蓝的、飘移不定的、笼罩着雾一般哀婉情调的国度。
父亲侯爵还叫人在台球室内张贴了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他想使儿子成为一个气宇轩昂、襟怀博大的人。但是,地图上冷寂的平板般的海面未能使他动心,勾起他回忆的倒是那片夜间的海洋,犹如一只保有体温、脉搏、血液和怒吼的巨大的黑兽。那可是夏夜里于极度烦恼之中轰鸣、狂叫的镰仓的大海啊!
右面是院线[插图]电车的轨道,眼下是朝阳辉映的工厂街,锯齿状的屋顶石棉瓦闪闪发光,各种机器的轰鸣混合在一起,发出海涛般的喧嚣。烟囱悲怆地耸立着,黑烟的阴影爬过屋顶,笼罩着夹在工厂之间的贫民街头的晒衣场。有的人家屋顶伸出一截平台,摆着众多的花盆。不知是哪里,总有一种光亮不停地闪闪烁烁,一根电线杆上电工腰间的铁钳,一家化学工厂窗户里梦幻般的火焰……一个地方的声音刚一停歇,接着敲击铁板的锤声又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五十二
这天,大和原野长满黄茅的土地上,雪片随风飞扬。说是春雪吧,又太淡了,犹如无数白粉虫飘飘降落,天空阴霾,那白色弥漫空中,微弱的阳光照射下来,这才看清楚是细小的雪粉。凛冽的寒气远比大雪普降的日子冷得多。
一切都显得异样的虚空和澄净,那些每天眼熟的景色,今日开始出现一种可怖的新鲜的姿影。这期间,他依然不住打寒战,一阵阵如锐利的银箭镞穿过脊梁。路旁的羊齿草、紫金牛的红果、随风飘拂的松叶,还有那主干青绿而叶子已经发黄的竹林、众多的芒草,以及贯穿其间有着结冰辙印的白色道路,一起没入前方幽暗的杉树林中。这般全然沉静的、每一角落都很明晰,而且含着莫名悲愁的纯洁的世界,其中心的内里,确确实实存在个聪子,她像一尊小小的金佛像屏住呼吸藏在这儿。然而,如此澄澈而生疏的世界,果真是她住惯了的“人世”吗?
五十四
所谓因果同时,就是阿赖耶识和染污法于现在一刹那同时存在,并且互为因果,过了这一刹那,双方共同化为无。下一刹那,又重新产生阿赖耶识和染污法,互相更换为因果。存在者(阿赖耶识和染污法)每一刹那因灭亡而产生了时间。由于每一刹那的断绝和灭亡,因而时间就会连续出现,这就好比点与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