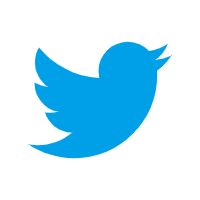这是最近做研究发现的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在agent的route decision中,究竟是personal issues重要,还是ambience重要?
前者认为人的偏好直接决定了其选择,因此分析偏好就能使得recommendation更加准确,更加能够避免misalignment。
后者则是我下意识决定的研究切入点,我认为处境更能决定选择,或者说,由于处境(具象地说,时刻、起终点、可用方式……)在被观测到后是稳定的,而人的偏好是变化、浮动的,因而处境属性与选择的对应关系强弱更好判定。不过,对于已有研究,显然前者的研究规模远大于后者。
权且按下这个问题,因为我联想到了另一件事。
近一年,有个词在某些场合被反复提及:neo authoritarianism。这个词本来是指代某种过渡阶段的ideology,但在当下似乎被赋予了某种新含义,演变成了和liberalism并驾齐驱的、人类体制优越性研究的重要课题。我觉得这也是ego和ambience的一种对垒形式。
这个更加形而上的问题目前没有公论,毕竟20多亿人还困在这个问题的解答环节中。
我当下的观点则是,如果从“后天”的角度看,那必然能得出人格受环境影响;如果从“先天”的角度看,也不能肤浅地认为基因影响人格,而是应该思考基因又由什么决定,比如natural selection这种显然应该归类为环境的因素对基因进行了严格的筛选。
一旦思考到这一层,从我本人出发,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这指示我至少应该做这么一件事:在introduction part中用类似causal inference的思路解释自己如此开展研究的原因。
这可真是个不得了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