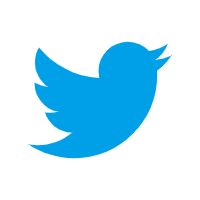对改变的渴望
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
不受欢迎者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的角色
人们评价一个种族、国象或任何其他群体时,往往是在该群体最低劣的成员中取样。这种做法尽管有失公允,却不是全无道理。因为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
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
穷人
会被失意感刺痛的穷人,一般都是新近才陷入贫困的,即所谓的「新穷人」。美好生活的记忆像火焰般在他们血管里燃烧。他们是失去继承权和遭剥夺的人,每有群众运动出现,就会忙不迭振臂相迎。
在苏联人民没有尝到过一点美好生活的滋味以前,苏联是不太可能爆发民众起义的。对苏联政权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将会是国家经济已有相当改善而极权统治因为某种缘故稍见松动之时。
那些最大声呼吁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乐于住在自由社会里的人。「失意者」因为受到自己的短处压迫,会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现有的种种限制。实际上,他们最深的渴望是终结「人人皆有自由」的现象。他们想要取消自由竞争,取消自由社会里人人都要经历的无情考验。
在自由实际存在的地方,平等是大众的热望。在平等实际存在的地方,自由是极少数人的热望。有平等而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而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模式。
促进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
在欧洲,犹太人是以个人的心态面对敌人,宛如飘浮在虚无永恒中的一抹微尘。但在巴勒斯坦,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一颗小原子,而是隶属于一个永恒的民族——这民族背后有一个古老得难以记忆的过去,面前是一个耀眼夺目的未来。
一个能干领袖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为他的追随者制造一种幻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从事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是在进行某种肃穆或轻松的表演,从而忘了生死问题的严重性。
对「现在」持贬抑的态度会让人培养出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适应良好的人都是差劲的先知。相反的,那些老是和「现在」过不去的人却别具慧眼,看得见改变的种子和蛛丝马迹。
轻信的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也喜欢欺骗别人。易相信和爱撒谎并不是小孩子才有的特质。因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看事物,他们就会发展出易上当和好骗人的特质。
在军队里,自我牺牲精神是通过义务感、戏剧性、团队精神、操练、对领袖的信仰而培养的。与群众运动的情形不同,这些手段并不是源自对「现在」的贬抑和对「自我」的排拒。因此,它们可以在一种清醒的氛围中展开。一个狂热的军人往往是狂热者从军的结果,而非军人感染狂热主义的结果。
团结催化剂
希特勒被问到有没有考虑过要把犹太人全部消灭时,他回答说:「没有……那样我们势必得另外创造一个犹太人。要紧的是有一个具体的敌人,而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敌人。」
我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一般不会寻找同好,甚至反而会把跟我们爱同一对象的人视为竞争者和侵犯者。但我们恨一个对象时,却总是会寻求有志一同的人。
要是哪一天美国人开始全心全意去恨外国人,就反映出他们已经失去自信心。
要是宣传的力量有人们想象的十分之一,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独裁政权就用不着那么暴虐。因为宣传要是有效,这些国家自会动用喧哗吵闹、厚颜无耻的一切宣传伎俩,却不会有秘密警察、集中营和大屠杀。
当强制手段毫不容情和持续不休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说服力,而且不只头脑简单的人会被说服,连那些以才智自傲的人亦复如此。例如,当俄国的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被克里姆林宫要求放弃信念和承认错误时,他们十之八九都是真心悔罪,而不只是口头敷衍。
失意者之所以追随一个领袖,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相信他可以把他们带到一片应许之地,不如说是因为领袖可以把他们带离开他们不想要的自我。顺服于一个领袖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的实现本身。至于领袖会把他们带到何处去,只是次要的问题。
一个共产党工委跟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家的共同点,可能大于他和一个共产党理论家的共同点。行动人之间的国际才是真正的「国际」。
群众运动用什么手段来强化和维系其依附者的不完整感,值得一提。其中一个手段是把教条提高到理性之上,这样,个人智慧就没有用武之地。另一手段是通过经济集权和故意使生活必需品稀少,让个人产生经济依赖。拥挤的居住或生活空间可以让人少些独立性,逼使每个人每天参与公共活动亦有相同功能。对文学、艺术、音乐和科学强力审查,可让即使有创造力的人也无法过上自足的生活。教诲信徒向教会、党、国家、领袖或信条献身,亦可以强化个人的不完整感,因为献身乃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务实的行动人
一个群众运动一般都是由言辞人为前驱,由狂热者实现,再由行动人加以巩固。如果这三种角色由不同的人接连担任,对一个群众运动来说通常都有好处;而一个群众运动想要长久存在,大概更是非如此不可。群众运动若是从开始到成熟都是由同一个人或同一批人领导,往往不会有好下场。
行动人用以巩固和维系新秩序的方法是折衷性的。他取法的对象不论远近,无分友敌。他甚至会向旧秩序取经,抄袭很多旧秩序用以维持稳定的方法,因而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与过去的连贯性。这阶段的一大特征是会出现一个绝对的独裁者,但之所以会这样,并不纯粹是当权者嗜权,这也是一种蓄意采用的策略。
良性与恶性的群众运动
把共产实验的成功归功于非共产世界中不受拘束的创造力,大概不是胡说。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灭亡以前理当可以与共产主义共存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这些人以为他们这样说是一个慷慨的让步。事实上,要是共产世界之外没有自由社会的存在,他们大概会发现有必要下令建立。
即便狂热的宗教人士和激进的无神论者也并非互不欣赏。其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吉洪主教有过很好的解释:「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比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世俗人更值得尊敬……完全的无神论者仅差一步就会是个宗教信仰无比热诚的人……但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人除恐惧以外没有任何信仰。」